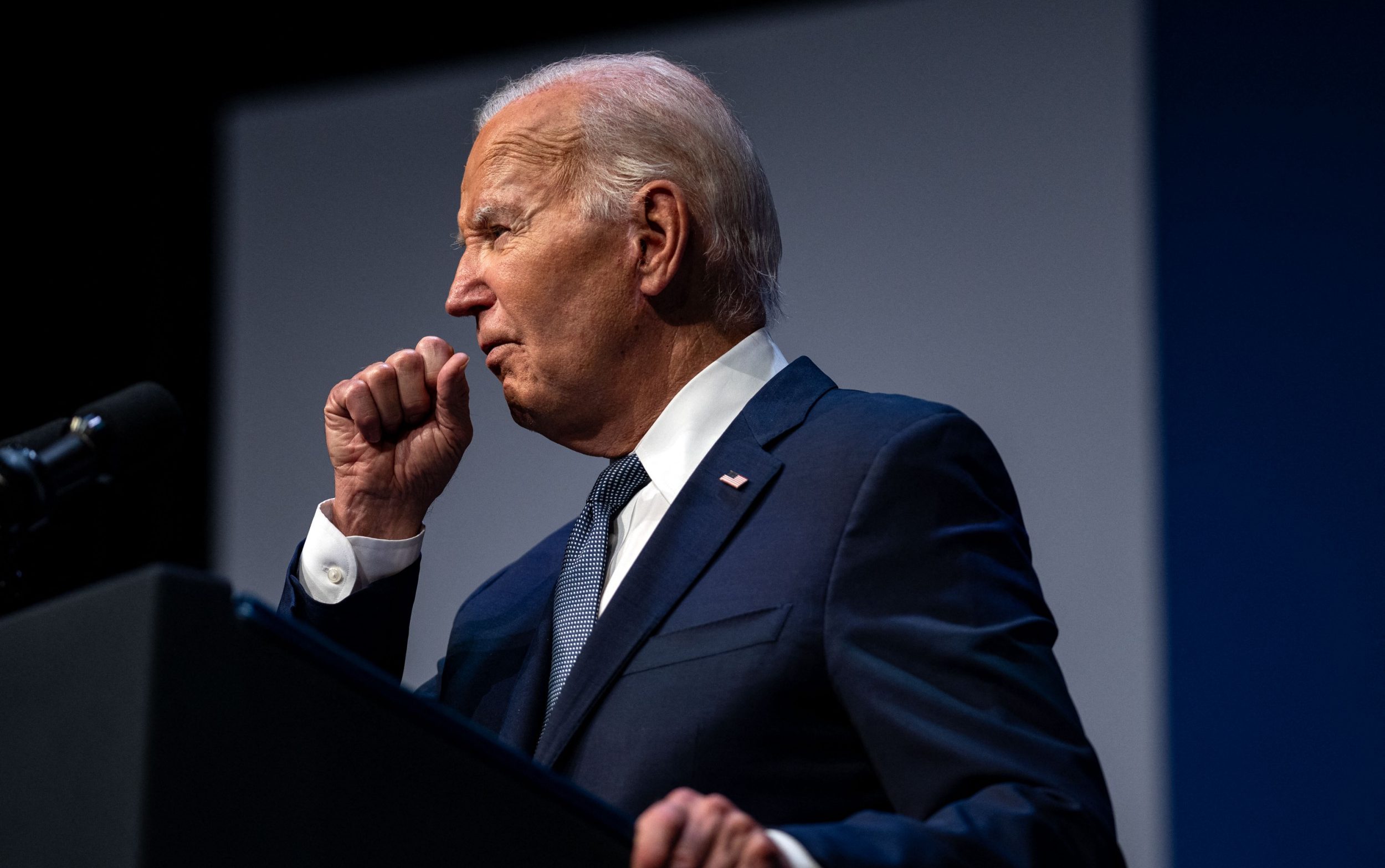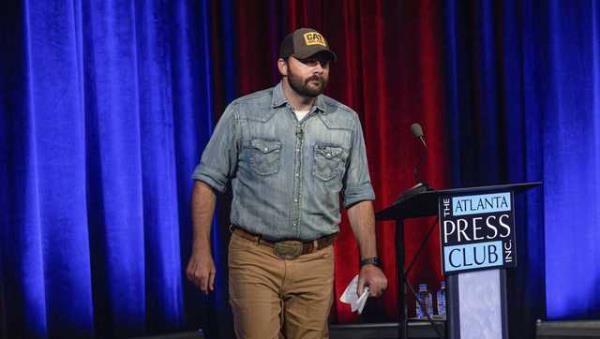作者:保罗·穆恩


分析:当谈到《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 the Tiriti to Waitangi)时,最常见的回答之一是,这是一个解释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完全公平的反应,除了历史解释通常需要遵守证据规则。
这不是对《条约》提出任何要求,然后诉诸个人解释的权威来维护其真实性的许可。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面临着一个矛盾的局面:条约研究的主体不断增长,但对其意义和目的的共识却越来越少。
因此,有必要调查一下近几十年来对《条约》产生的一些较为常见的误解。这不会导致对《条约》作出明确的解释。但它可能会消除目前在更好地理解它的道路上的一些障碍。
一个共同的观点坚持认为,《条约》的英文版本和Māori版本在根本上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在主权这一核心问题上。
但是,对1840年之前英国殖民政策的研究表明,英国希望签订一项条约,使其能够将管辖权扩大到居住在新西兰的臣民。
它无意统治Māori或篡夺Māori主权。在这个关键点上,这两个版本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合同法中引申而来的条款对抗原则是指可以以不利于合同起草者的方式加以解释的模棱两可的条款。
但是,在将这一原则适用于《条约》方面存在若干问题。首先,条约是不同于合同的法律文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国际法中使用这一原则来解释条约的例子相对较少。
第二,由于《条约》的英文本和Māori本在Māori保留主权方面没有重大的实质性差别,因此没有必要适用这样一项原则。
第三,根据国际法,条约不应以对抗的方式解释,而应以善意的方式解释(公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因此,与其当事方就《条约》的含义进行斗争,不如要求它们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对立。
没有任何兰加蒂拉(酋长)通过该条约放弃对自己人民的主权。这也不是英国的本意——因此英国在1839年8月承认了哈普伊(亲属团体)的主权,并在条约中保证了酋长的权力将得到保护。
英国只是想要对自己在殖民地的臣民拥有管辖权。这就是所谓的“原旨主义”解释,即遵循1840年对《条约》的理解。
这有几个限制:它排除了条约原则的出现;它错误地假定所有有关各方在签署《条约》时对其意义都有相同的看法;至关重要的是,它忽略了所有随后的历史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条约关系以多种方式演变。原旨主义的解释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英国签订条约的动机在1839年就已经明确了,然而在接下来的185年里,错误的动机进入了历史的血液,并继续流传。
英国想要的是对居住在新西兰的英国人适用其法律的权利。它还打算“教化”Māori(通过建立短暂的土著保护者办公室),并保护Māori土地免受不道德的购买(条约第二条中的优先购买权条款)。
同时,英国希望在一个群体的行为影响到另一个群体的行为时,给予Māori与英国国民同样的权利(如1842年的maketji案件,涉及到一名年轻的Māori男子被判谋杀并被处决)。
该条约不是对法国对新西兰的威胁作出的反应。这不是企图征服Māori,也不是用诡计欺骗他们。
在过去二十年中,一些人声称有一个“真正的”条约- -所谓的“利特尔伍德条约”- -被隐瞒了,因为它包含了一套不同的规定。这种阴谋论的说法很容易被驳斥。
利特尔伍德条约的案文是已知的,它只是实际条约的手写副本。而且,最明显的是,它不能在没有人签署的基础上被视为条约。
另一个普遍的误解是,《条约》有第四条,据称保障宗教自由。该条既没有出现在《条约》的Māori或英文文本中,也没有证据表明签署国将该条视为协定的一项规定。这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种说法,但缺乏任何证据或法律依据。
最后,有人认为《条约》支持民主进程。事实上,该条约在该殖民地开创了一个非代议制政权。正是1852年的《新西兰宪法法》赋予了该国一个民主政府- -顺便说一句,这项法令没有提及《条约》的规定。
这个列表并不详尽。但是,在消除解释不佳的领域时,我们可以增加就《条约》进行更为知情和富有成效的讨论的机会。
Paul Moon是奥克兰理工大学历史学教授
本文最初由The Conversation发表。